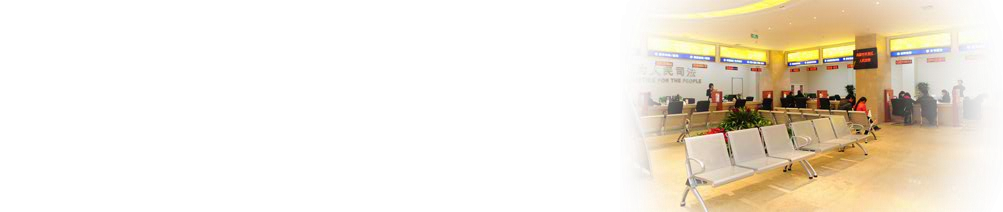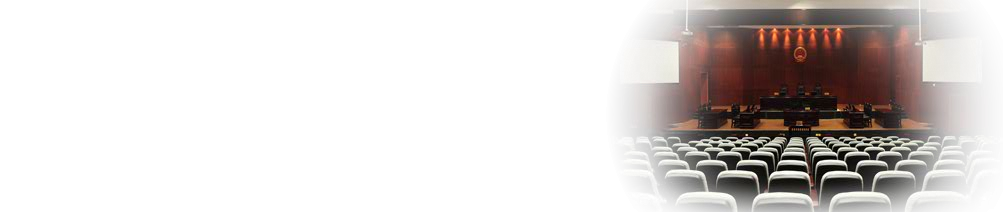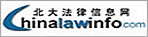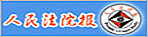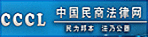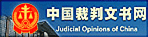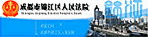【示范点】
强制医疗制度的适用规则之探讨与明确。
【案情】
被申请人徐某在2007年下半年开始出现精神异常,表现为凭空闻声,认为别人在议论他,认为有人要杀他,紧张害怕,夜晚不睡,随时携带刀自卫,外出躲避。因未接受治疗,病情加重。2012年11月18日4时许,被申请人在其经常居住地听到有人开车来杀他,遂携带刀和榔头欲外出撞车自杀。其居住地的门卫张某得知其要出去撞车自杀,未给其开门。徐某见张某手持一部手机,便认为张某要叫人来加害自己,遂当即用携带的刀刺杀张某身体,用榔头击打张某的头部,致张某当场死亡。2012年12月10日,徐某被公安机关送往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012年12月17日,成都精卫司法鉴定所接受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的委托,对徐某进行精神疾病及刑事责任能力鉴定,鉴定结果为:徐某目前患有幻觉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徐某2012年11月18日4时作案时无刑事责任能力。2013年1月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对被申请人的病情作出证明,证实徐某需要继续治疗。
【审判】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强制医疗决定书认为,本案被申请人徐某实施了故意杀人的暴力行为后,经鉴定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其妄想他人欲对其加害而必须携带刀等防卫工具外出的行为,在其病症未能减轻并需继续治疗的情况下,认定其放置社会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检察院提出对被申请人强制医疗的申请成立,予以支持。关于诉讼代理人提出被申请人是否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应由医疗机构作出评估的辩护意见,经查,在强制医疗中如何认定被申请人是否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需要根据以往被申请人的行为及本案的证据进行综合判断。而医疗机构对其的评估也只是对其病情痊愈的评估,法律没有赋予它对患者是否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性方面的评估权利。本案被申请人的病症是被害幻觉妄想症,经常假想要被他人杀害,外出害怕被害必带刀等防卫工具。如果不加约束治疗,被申请人不可能不外出,其外出必携带刀的行为,具有危害社会的可能,故诉讼代理人的意见不予采纳。遂于2013年1月24日作出对被申请人徐某实施强制医疗的决定。
【评析】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快节奏的生活、日益多元的价值观念及不断加剧的社会分化等因素导致社会普遍的心理紧张、失衡及无所适从,使得当前我国精神病患者人数不断攀升,其中暴力型精神病人实施危害社会的案件时有发生。精神疾患者虽不具备危害社会及他人安全之法律意义上的意思表示,但其无意识之暴力行为却给受害者家庭造成无尽的伤痛,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无穷的伤害。为充分保障公共安全和人民幸福,避免具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继续侵害社会和他人,国家有必要对此类精神病人实施强制医疗。
事实上,我国刑法对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精神病人予以强制医疗已作出原则性规定,该法第十八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但其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的适用程序、具体实施语焉不详,对于不追究刑事责任后的处理机制付之阙如,这在实践中难以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新刑诉法将强制医疗制度以特别程序的方式纳入其中,实现了强制医疗制度的法治化与司法化。司法强制医疗制度本质上是对精神病人人身自由进行限制的一种社会防卫措施,因此,虽然强制医疗并非刑罚之一种,但毕竟是对人身自由实施了干预、限制或羁束,故适用及实施该制度应持慎重态度。下面将结合本案,对强制医疗制度的适用条件及程序问题进行分析论证,以对司法实践有所助益。
一、适用强制医疗制度之要件
按照新刑诉法第二百八十四条“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之规定,适用强制医疗制度应同时具备以下三个要件:
(一)行为要件。“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应为适用强制医疗制度的行为要件。对此,可从如下两方面理解把握:一是,行为人已着手实施了符合犯罪的客观违法性特征之暴力行为,且若是由有刑事责任能力者实施该行为则已构成犯罪。二是,该行为必然侵害到下列两个法益之一:1.公共安全,即行为人实施了危害多数或不特定人的健康甚至生命或者公共社会的和平与安宁之行为,并且该行为导致了相应的侵害结果或危险发生;2.公民人身安全,即该行为危害到特定人的健康、生命安全、人身自由等基本人权及其生活的安宁、安全,且此类行为要求造成的具体侵害结果应达到严重程度,比如暴力致人重伤、死亡等。
本案被申请人徐某因一直未接受治疗,精神疾患病情加重。2012年11月18日4时许,被申请人在其居所幻听到“有人开车来杀他”,遂携带刀和榔头欲外出撞车自杀。其居住地门卫张友发得知其出去要撞车自杀,未给其开门。徐某见张友发手持一部手机,便认为张要叫人来对其加害。徐某当即用携带的刀刺杀被害人张友发身体,用榔头击打张的头部,致被害人张友发当场死亡。被申请人徐某的上述杀人行为,属于对特定人生命权的侵害、剥夺,已达到严重的危害性后果,故应认定符合适用强制医疗制度之行为要件。
(二)适用对象。“经法定程序鉴定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是强制医疗制度适用对象方面的要求,具体分解来看,满足该要求应具备以下条件:第一,适用对象须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且依法也无需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依据刑法第十八条之规定,强制医疗制度的适用对象具体包括:(1)实施行为时不能辨别、控制自己行为的间歇性精神病人;(2)完全不能辨别、控制自己行为的完全不负刑事责任之精神病人。第二,该对象是否属于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须经过法定程序鉴定。第三,行为人实施暴力犯罪行为发生在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之后,反之,若行为人在精神正常时实施犯罪而其后又患上精神病的情形则不应适用该特别程序。
本案被申请人徐某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出现精神异常,2012年11月18日4时许,在精神异常状态下持凶杀人,致被害人张友发当场死亡。2012年12月17日,成都精卫司法鉴定所接受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委托,对徐某进行精神疾病及刑事责任能力鉴定,同月26日该所出具成精司鉴所(2012)病鉴字第105号鉴定意见书,载明:1.被鉴定人徐某目前患有精神分裂症,幻觉妄想型;2.被鉴定人徐某2012年11月18日4时作案时无刑事责任能力。因此,被申请人徐某属于应予以强制医疗的适格对象。
(三)危险性要件。“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则规定了强制医疗制度的危险性要件。危险性是指强制医疗制度适用对象已实施了暴力行为且具有再次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可能性,即该类精神病人具备人身危险性。具体可通过如下表征进行认定:其一,该精神病人实施暴力行为的性质、采取的方式与手段、侵害的对象以及造成的危害后果或程度等情况;其二,该精神病人的性别、年龄、身体状况、精神疾患之性质与状况、过往危害社会行为纪录等情形。
本案被申请人徐某在2007年下半年即出现精神异常,经常性幻听、“幻(被)杀”,病情严重且发案前未接受治疗;2012年11月18日在精神错乱状况下行凶杀人且手段残忍,并致人死亡;2013年1月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对被申请人的病情作出证明,亦证实徐某需要继续治疗。综上,足以认定被申请人徐某具有“继续危害社会” 的极大可能性。
二、适用强制医疗制度之程序性规定
(一)启动程序。新刑诉法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公安机关发现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应当写出强制医疗意见书,移送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移送的或者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发现的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 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 可以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 依据该规定,启动强制医疗程序包括两种情形:一是由公安机关移送审查或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发现涉嫌犯罪的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应向法院提起强制医疗申请;二是在案件审理阶段,受理法院发现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可依职权作出强制医疗决定。
本案是由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1月22日以成武检强制医申(2013)第1号申请书向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申请对被申请人徐某强制医疗后,本院审查后依法立案受理的,应属于上述启动模式的第一种情形。
(二)司法审理程序。刑诉法修订之前,公安、检察机关决定实施强制医疗的程序不透明,甚至连听证、质证等公开环节都无需举行。由于适用强制制度直接关系到对行为人人身自由之切身利益,且判断、认定行为人是否符合适用要件本身也相当复杂,所以采用合议庭制进行司法审判更有利于保护当事人基本人权,也有利于保证案件质量,故新修订的刑诉法第二百八十六条作出如下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强制医疗的申请后,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人民法院审理强制医疗案件,应当通知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可见,该条还规定了告知程序和“强制代理制度”,因为被申请人或被告人由于罹患精神疾患、缺乏诉讼技能甚至人身已受到羁束,很有可能不能有效参与到审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所以对于强制医疗制度设计而言,告知程序和“强制代理制度”显然是必要的,也是尊重和保障人权之具体体现。
本案采用合议庭制进行开庭审理过程中,被申请人徐某的法定代理人潘长秀、指定代理律师成安、田银行均到庭参加诉讼,法院围绕着“被申请人是否符合强制医疗的要件及是否应予对其实施强制医疗”等核心问题进行了法庭调查,控辩双方围绕本案核心问题展开了法庭辩论,本案的司法审理程序是公开、公正的,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三)庭审监督程序。在审理强制医疗案件过程中,检察机关应派员出庭,对庭审活动是否合法、规范进行监督。对于法院审理程序违法甚至实体违法的强制医疗决定,检察机关作为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部门,可以充分利用纠正违法检察建议书或审理建议书等形式,对司法审判过程中的违法问题进行监督、纠正,法院对此依法应作出书面回应与恰当处理。
本案申请人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检察院委派代理检察员丛林出庭参加诉讼,宣读强制医疗申请书并参与法庭调查及法庭辩论,这既是检方履行强制医疗制度规定的检方责任之表现,也是检方对法院审理强制医疗案件进行监督的一种体现。
(四)救济程序。新刑诉法第二百八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强制医疗决定不服的, 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本款为对强制医疗决定不服的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关于对决定不服提供的救济程序。应该说,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是新刑诉法设置一种特殊程序,它既具有司法程序的特点又具有明显的行政方面之特征,故引入了行政复议程序在理论上、实践中都是必要的。
此外,依据新刑讼法第二百八十八条之规定,实施强制医疗的机构应定期对被强制医疗人进行诊断评估,对于已不具备人身危险性,无需继续实施强制医疗的,应及时提出解除意见,报请决定强制医疗的人民法院批准。当然,被强制医疗人及其近亲属也有权依法申请予以解除。再者,依据新刑诉法第二百八十九条“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之规定,检察机关应积极介入,对其执行情况实行有效的法律监督。
本案审理过程中,被申请人的诉讼代理人提出“是否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应由医疗机构作出评估,本案没有医疗机构的评估报告,认为对被申请人的强制医疗的证据不充分”之辩护意见,实则是对新刑讼法第二百八十八条的错误理解,强制医疗机构作出的鉴定或评估意见仅针对被强制医疗人病情状况或是否继续治疗等精神病医疗专业问题,法律没有赋予其对患者是否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性问题作出评估、认定的权利;相反,定期对被强制医疗人应当进行诊断评估系强制医疗机构之法定责任,本案被申请人徐某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在徐某随后的强制医疗期间,为维护被申请人人身权益可随时依法寻求司法救济。
本院作出的强制医疗决定书在结尾部分,依法告知了当事人申请复议的权利及复议期间、复议法院等内容,复议期满,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均未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现该强制医疗决定书已生效。新刑诉法实施以来,我院专门组织了刑庭法官及法官辅助人员对相关新制度、新规定进行了理论学习与模拟庭审演练,并对有关案由、案号、庭审准备、归卷等工作作了详实的安排,而本案是新刑诉法实施后本院及全省办理的首例强制医疗案件,应该说案件的处理是妥当的,实现了“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